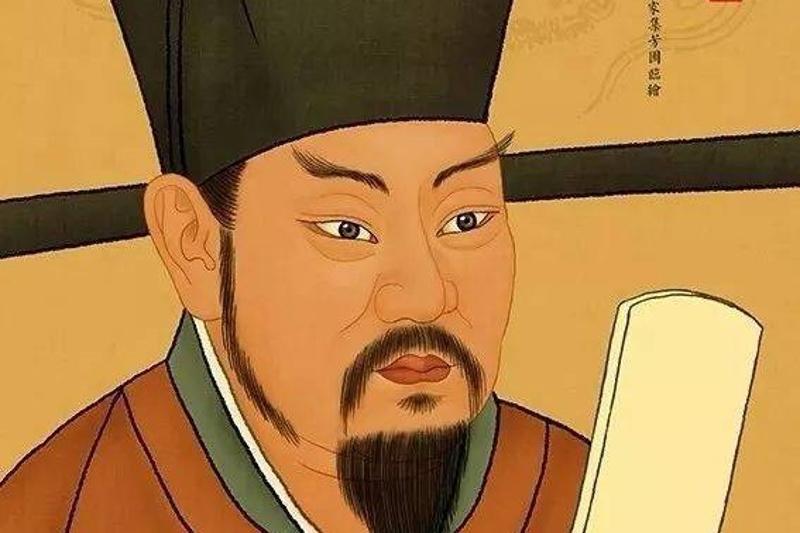范缜
范缜,他对“神不灭”的批判和对“神灭”的论证,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范缜"神灭论"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当时统治阶级上层,把佛教当成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法宝。王公贵族、门阀士族几乎无不信仰佛教,而佛教徒中的上层僧侣也与统治者上层结合起来,出入宫廷,直接参与政治统治。
些寺院、僧侣不仅耗费大量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而且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同时由于僧侣人数增多,僧侣可以免税、免役,致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使一般劳动人民纳税、服劳役的负担大大加重。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当时的劳动农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他们不但反对世俗地主阶级,而且还特别地反对僧侣地主阶级。僧侣中的下层,大都是破产农民、不得已而投靠寺院的劳动人民,也不断从佛教内部起来,与农民起义军一起反对世俗与僧侣大地主的统治。
同时,由于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僧侣地主与一般世俗地主之间也产生了争夺土地和劳力的矛盾。佛教寺院耗费大量社会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
最初反对佛教神学的理论,主要是从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等政治、道德规范着眼,认为佛教的出世主义与此不合。直至东晋时期,反佛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也还是“沙门”应不应该“敬王者”,即佛教僧侣对最高封建统治者,应不应该行跪拜礼的问题。批判“沙门不敬王者”的主要理由也还是说,如果佛教僧侣不敬王者,那么“王教不得一,二之则乱”,是从维护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着眼的。
在范缜以前,已有许多无神论思想家对佛教宣扬的轮回、报应等理论进行了批判。例如戴逵就对因果报应说提出了质难。他说有的人一生言行都按照道德规范去做,可是得到种种不幸的遭遇;有的人一生胡作非为,却获得荣华富贵,子孙繁盛。所以,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他还根据中国历史记载和传说中的大量故事和事实,证明因果报应是不存在的。此外何承天还根据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实,驳斥因果报应的荒谬。他说,譬如,鹅在池塘中游戏,吃一些草,其他生物它都不侵犯,可是厨师抓住它就宰烹,很少能有幸免的;燕子飞来飞去,专门找各种飞虫吃,可是人们都喜爱它,即使把窝做在屋檐下,也不去惊动它。何承天这里用的例子虽然并不恰当,但从他揭露佛教认为“杀生”会招来恶报,反对因果报应说来讲,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必须有一个主体承担者,没有一个主体承担者,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也就落了空。佛教与中国传统道教所谓“长生不死”、“肉体成仙”不一样,他并不否认肉体的死亡。既然肉体不能成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承担者,那么承担轮回、报应的主体,只可能是一种永远不灭的精神主体,即所谓“神”。因此,“神不灭”是佛教神学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迷信的理论基石。不能彻底驳倒“神不灭”论,也就不能从理论上完全摧垮佛教神学。
戴逵在其《流火赋》中对“神不灭”思想提出了置疑性的批判。他说生命知觉的存在是依靠着气,就像火焰的燃烧必须依靠木柴一样。然而木柴和气都有用尽的时候,怎么能说火焰和生命知觉却能永久延续下去呢?火要依靠于木柴,木柴烧得差不多了,火就微弱,木柴烧完了,火也就灭了,即使精神有多么神妙,但离开了形体也不能单独地存在下去。用薪火喻形神,虽能说明神灭的理论,但它带有很大的理论缺陷。
这样他们就不是把神看做只是形(人体)的一种特殊性质、作用,因此也就不能从理论上根本说明神必须依赖于形,形亡神灭的道理另一方面,一块薪烧完了,另一块薪可以接着烧,火可以从一块薪传到另一块薪。但是形与神的关系,神绝不能由一个形体传到另一个形体上去,所以这种比喻是很不确切的。范缜《神灭论》所批判的是整个佛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而直接的对立面则是梁武帝。
范缜的无神论学说
范缜反对佛教神学的斗争,也是从反对因果报应开始的。范缜用自然的偶然论来反驳因果报应说。他认为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生就如同树上的花朵一样,虽然一起开放,但随风吹落,有的花被吹落到厅堂上,漂亮的坐垫上;有的花却被吹落到厕所里。人生的贫富贵贱完全是一种偶然的遭遇,绝不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认为“前生”做了善事,今生享受富贵;前生做了恶事,因此今生贫贱。这种理论正是为统治者的特权地位,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作论证的。范缜认为贫富贵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虽然这在理论上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现象,同样也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范缜用它驳斥因果报应说,蔑视门阀士族的特权地位,也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范缜《神灭论》的主要论点如下:
形神相即。范缜论证神灭观点的第一条理由就是“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即”是不相分离的意思。这是说,神和形,形和神是不能分离的。形和神是“名殊而体一”,即形和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范缜把这又叫做是“形神不二”,或形神“不得相异”。这是范缜对形神关系的一元论观点。是针对当时一些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形神二元论的。例如,佛教信徒曹思文认为神与形是可以分开而独立存在的,生只是形与神暂时凑合在一起,死后尸体(形骸)留下了,而神则可以转移到别处去。这就把形和神完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实体,从而证明神可以是不灭的。
佛教徒还用梦幻来证明“形神非一”、“灵质分途”的形神二元论观点。佛教徒用梦境来论证形神二元论是有其认识上的根源的。恩格斯在分析灵魂不死思想时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范缜对佛教徒用梦幻论证“形神非一”的二元论也进行了驳斥。说明即使做梦也离不开形体,然后才能享受。他驳斥“神游于蝴蝶”说,如果真变成蝴蝶,那么醒来时身边应该有死蝴蝶的形体,但实际上是没有,可见梦只是一种虚假的幻景而已。范缜虽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做梦现象的本质,但它驳斥了形神二元论,坚持了形神一元论,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
当然坚持形神一元论,也还不能说就是无神论。例如:梁武帝讲的“心为用本”也是形神一元论,但他是把“心”作为本,是在宣扬有神论的。范缜则相反,他在《神灭论》中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这里明确地表明形是第一性的,神是依赖于形才能存在的,因此,形谢(死亡)神也就消灭了。这就是无神论的形神一元论。
形质神用。范缜进一步用“形质”“神用”的观点论证其无神论的形神一元论。形是实体,是神的主体,而神只是形的作用,由形派生出来的。既然只有形体才是主体,而神只是形体的作用,那么作用决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主体消亡了,作用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这就克服了以前无神论者把形神看做“精粗一气”,两种不同物质的理论缺陷,堵塞了神可离形而独立存在的漏洞,从而使神灭论的理论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范缜对形神关系唯物主义论证的最大贡献。范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神和产生它的主体形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有刀刃才有锋利,有锋利才称得上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不存在了也还有锋利,那怎么能说形体死亡了而神还存在呢?这个比喻的结论,有力地打击了佛教“形神相异”、“神不灭”的形神二元论。
佛教信徒萧琛企图用“钝刃”“利灭而刃存”来驳难范缜刃利之喻,这一驳难反而证实了范缜的思想。所谓刀有刃就是说有锋利,无锋利即不能说有刃,“钝刃”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人之质有知,木之质无知。范缜不仅一般地讲到精神是形体的作用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精神作用并不是所有的“质”都有的“用”,而是只有活人的“质”才具有的特定的“用”。
当时佛教信徒为了驳难范缜“形质神用”的观点,他们企图用“质同”“用异”的诡辩来难倒范缜。他们说,“木之质”与“人之质”是一样的“质”,为什么木无知而人有知呢?范缜反驳说,所以有知与不知的不同(“用”不同),就是因为“质”不同。人的质与木的质是不同的,所以人有知而木无知。人与木的质是不同的质,所以才有有知与无知的不同。精神现象(“有知”)只是人之质所具有的特定属性,而不是所有质都具有的。
佛教徒于是又反问范缜道,既然只有人的形体才有知觉作用,那么人死后,形体还在也还应当有知觉,可见灵魂并不随形体死亡而消灭,神是不灭的。这与上述驳难是同一性质的诡辩。范缜仍然坚持“质”不同所以“用”不同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此进行反驳。范缜说,活人和死人的质是不同的。虽然人死后形体不是一下子消灭尽,但死人形体与活人形体是有质的区别的。这就如同活着的花木能开花结果,而枯树凋谢不能再开花结果一样。死者的骨骼如同木头的质那样,所以与木头一样,没有知;活人之所以有不同于木头的知,那是因为活人的质与木头的质是不同的。
范缜这里把精神活动规定为只有活人的形体才具有的特定的质,这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卓越理论成就。这样,就从理论上摧垮了宗教所宣扬的天堂地狱,今生行不善,来生变牛马的轮回、报应等迷信思想。
知、虑皆是神之分,不能离“本”(形体)而有知、虑。范缜认为,精神活动必须依赖于形体,是形体的作用。关于精神活动,范缜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感受痛痒的“知”,即感觉、知觉;一类是能判断是非的“虑”,即思维。范缜认为这两类精神活动有程度上的差别,“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但这两类精神活动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同是人的形体的统一的精神活动的两个方面,即所谓“皆是神之分也”。
范缜在这里坚持“知”“虑”“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的观点,是为了反对那种把“知”“虑”分离、对立起来,认为“知”虽要依靠手足等形体,而“虑”却可以不依靠形体的“知”而独立的错误观点。范缜进一步分析了所以有“知”“虑”程度上的差别,是因为“知”“虑”依据于人体的不同物质器官。这里,范缜还认为“心”与手足等器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如同“手足虽异,总为一人”,而只有作用上的不同。“心”与手足的差别,也就像眼与耳的差别一样是“司用不均(同)”,而不是“心”与手足等作用有什么根本不同的地方。
佛教徒用“虑思无方”,即思维不受一定空间的限制,反对范缜的“虑”为“心器所主”的观点,提出“虑体无本”的观点。那是否说,张甲的精神可寄住于王乙的形体中去,李丙的精神可寄住到赵丁的形体中去呢?范缜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范缜强调任何精神活动,一定不能脱离特定的物质形体,这是较为彻底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由于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范缜不能科学地解释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他错误地把“心”脏当作思维器官。同时,他也不能科学地阐明思维活动与感觉之间的关系。
除上面讲到的以“心脏”为思维器官,不能科学说明思维与感觉的辩证关系外,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范缜用自然的偶然性理论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这有它一定的理论作用。但以此来解释社会贫富贵贱差别的形成,则是根本错误的。用自然的偶然性来解释人的社会差别,不仅不能说明人的贫富贵贱差别的真正原因,反而会使人们产生无所作为,一切听凭偶然的机会的消极思想。结果和宿命论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一样,都不能引导人们去对产生贫富贵贱差别的社会原因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找出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
范缜虽然坚持了精神活动不能脱离人的物质形体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他根本不能了解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道理。因此,当他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们知识、才能上的差别时,得出了“圣”“凡”不同器的错误结论。范缜主观上企图用唯物主义原则来解释的问题,在客观上却达到了与唯心主义先验论同样鼓吹天才论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范缜以“神灭”论的根本理论,基本上否定了鬼神的存在。他不相信人死变成鬼神的有神论。但是,他不敢完全否定传统经典中所记载的祭祀鬼神的活动。他同样肯定了“神道设教”的必要性,认为提倡祭祀鬼神,这是“圣人之教然也。即目的在于顺从孝子的情感,纠正偷懒和轻浮的倾向,这就是“神而明之”的意思,即假设一个最高的天帝和灵魂存在,从而把圣人的教化和统治神圣化。同时,他虽然不承认人死后变成的“鬼”的存在,却又认为有一种与人不同的,叫做“鬼”的生物存在。这些也都是范缜无神论思想不彻底的方面。
范缜的《神灭论》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佛教有神论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的批判是有力的、彻底的。但唯物主义无神论在理论上战胜了宗教有神论,并不意味着宗教由此就会消失。因为宗教的存在不仅有它认识论上的根源,而更主要的是有它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