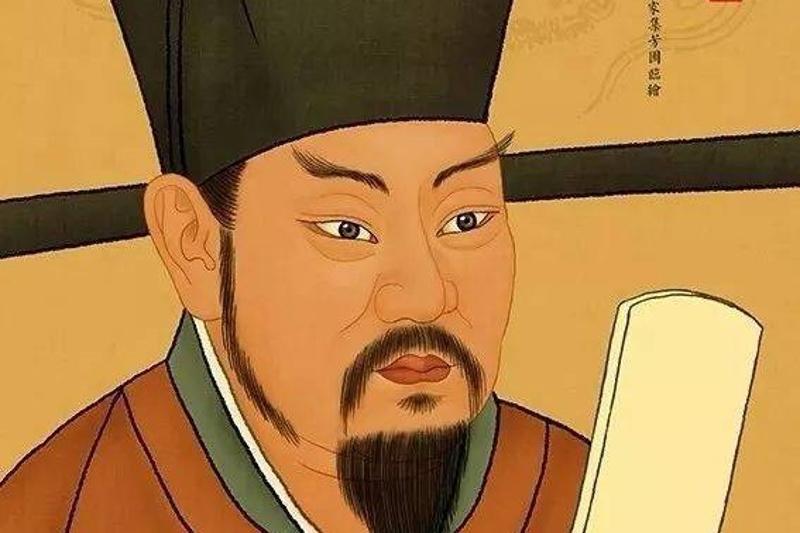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思想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乔达摩,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国王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佛”是所谓“觉悟”的意思,指他觉悟了“绝对真理”。(宇宙人生的真谛)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与其他一切宗教一样,都是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尚不能作出正确说明,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情况下的产物。佛教创造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把现实生活看做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思想,并宣扬极乐净土(天堂)、地狱等宗教世界。佛教哲学理论,归根到底是为其宗教说教作论证的。
当时佛教主要宣扬的宗教思想是: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和神不灭论等宗教观点。其佛教哲学思想则主要是大乘空宗主张的一切皆空、“性空幻有”的思想、大乘空宗的这种理论与玄学贵无论所主张的世界本原是“无”的理论相似。因此,它很容易与玄学结合起来,宣扬空宗思想,而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惠远的佛教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
慧远,他是东晋最博学的佛教学者道安的弟子。道安一生致力于整理佛教经典,辨别真伪,编纂了佛教丛书的目录,组织了佛经的翻译工作,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他还确立僧侣集体生活的戒规。
惠远之前,道安对佛教讲“空”的理解基本上与王弼的玄学“本无末有”、“崇本息末”的“贵无”思想差不多。道安虽然讲,万物的形成和变化是“出于自然”,没有一个“造物主”(“岂有造之者哉?”),这比简单地认为世界是有一个人格神的造物主创造的宗教说教要巧妙多了。但他认为在有万物之前世界是一个空无状态。在这里虽然他表面上也否定无中生有的说法(“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但他认为“无”、“空”是万物的根本,在万物之“先”、“始”,而且要人们“崇本息末”,不要执著于物质世界(“滞在末有”),而要认识和回复到世界本无的境界(“宅心本无”)。这就是道安所理解的般若空观的思想。
慧远进一步发挥了道安的“本无”理论。他认为,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根源于精神感情活动,如果不使感情发生,也就没有万物的发生、变化。而要使感情不发生,就必须认识万物以至人的本性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也就是说是“本无”的。为什么“法性”是“无性”,而“无性”的“法性”又能生出万物呢?万物的生成都是各种“因缘”(条件)的暂时凑合,没有独立的本性,所以虽说是“有”,而实际上是“无”。
佛教所谓的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以永恒不变为“性”的,而要达到宗教的最高精神修养境界就必须体认这个实体,也就是说要超脱一切现实生活和世俗的见解。这样,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和超脱一切现实变化的最高精神修养境界,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佛教的最高实体也就是一种超脱现实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最高精神境界。
“泥洹”(新译作“涅槃”)是佛教所宣传的一种绝对安静、无思无念的最高神秘精神状态。只有体认了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的人,才能不以生命来拖累他的精神世界;只有根本超脱现实世界一切俗务的人,才能不以各种情感来拖累他的生命。这样,就可以达到停止一切思虑和情感活动(“冥神绝境”),即“涅槃”的境界。
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反佛斗争中提出的问题,着重论证了两个问题:
论证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一致性;
进一步论证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的理论基础——灵魂不死不灭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表面上是要解决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则反映了当时僧侣地主阶级与一般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佛教到东晋南北朝发展极盛,大小都市庙宇林立,出家僧侣数目剧增。他们大量占有土地和劳力,并且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与一般世俗地主也发生了矛盾。因此,当时产生不少激烈反对佛教的思想家。最初,反对佛教理论的思想家,大都是从佛教是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观念不合这点着眼的。僧侣“剃头发,被赤布”,“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是“违圣人之说,不合孝子之道”。其次,根据佛教教义,僧侣是出家人,是超脱了世俗的,对皇帝也不行跪拜礼,这也触及了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慧远着手来解决这个矛盾。僧侣出家表面上看来背离父母子女的天生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违背孝的道德规范,同样,僧侣形式上不对帝王行跪拜礼,实际上也并没有失去敬的原则。他虽然没有处于王侯的地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他的作用已经是协助了帝王对人民的治理。本来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并没有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它们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制度服务的,只是在理论形式上和采用的方法上有某些不同和冲突而已。慧远实际上是调和两者的矛盾,而使两者合而为一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佛教宗教的根本理论问题。佛教用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来为社会十分不平等的贫富贵贱现象的合理性作论证,宣扬一个人现世或下世的贫富贵贱,都是他自身前世或现世为善作恶的结果。根据这种宗教的虚构,善恶行为的因果报应,前世、现世、来世的轮回,必须有一个主体的承受者。关于这样一个虚构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在印度佛教中是不明确的。因为根据佛教一切皆空的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承认有一个独立的、不灭的精神实体存在,同样也会引起种种烦恼以至阻碍超脱轮回、报应而成佛。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就叫“我执”,也必须破除。但没有一个承担者,轮回、报应的虚构就将落空。因此,印度佛教各派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曲折、隐晦、神秘的说法竭力回避把轮回、报应的承受者看成一个实体,而把它描绘为一种无实体的意识活动或行为作用等。实际上,不管他们如何讲,总还是一个承受轮回、报应的精神主体。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一般人根据其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理论,认为精神(灵魂)不死不灭似乎是佛教理论的当然前提。
慧远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宗教说教深信不疑,他从佛教一切皆空的观点,进一步论证了因果报应的思想。慧远就认为人所以遭受一切不幸的恶果,都是由其自身陷于“无明”(即愚昧)和“贪爱”等情感造成的。这种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慧远认为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的是当世就受报,这叫“现报”;有的来世受报,这叫“生报”;有的“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叫“后报”。佛教这种轮回、报应的说教也比中国传统的只讲现世受报,或父母作善恶而子孙受报应的说法要精致得多。这里讲的一世就是一个轮回,只要你不去掉“无明”、“贪爱”等世俗的感情,你就永远不能超脱“轮回”,生生世世摆脱不了现实世界的种种苦恼。只有相信佛教的说教,把一切都看成“空”,才能不为“无明”、“贪爱”等错误感情所牵累,从而超脱轮回,投身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天国),永证佛果(成佛)。
承认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教,就必须要有一个主体的承受者。因此,必须奠定其理论基石——神不灭论。慧远对于神不灭论的论证主要有以下论点:
神是一种非常精灵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具体形象的,所以不可能像具体的万物那样用形象来表示,连“圣人”也只能说它是一种十分微妙的东西。神的作用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神与万物相感应,变化无穷,而神自身则是“无生”、“无名”的。
其次,神既然是不灭的,那么神是如何从一个形体转到另一个形体中去的呢?慧远认为,这就像火传给薪一样。把形神关系比作薪火关系,原是东汉思想家桓谭最先使用的。桓谭用薪火之喻原是说明“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的“形亡神灭”的原则的。慧远就是用火由这块木柴传到另一块木柴,来论证神也可以由这个形体传到另一个形体去的。慧远在这里是搞了一个逻辑上的诡辩,因为他所讲的木柴或形体都是指的某一块具体的木柴或某一个具体的形体,而当他讲到火由这块木柴转到另一块木柴,或神由这个形体转到另一个形体时,他就不讲某一具体木柴的火或某一具体形体的神,而是讲的一般的火或神。因此这样的比喻在逻辑上是根本错误的。慧远并不理会这种错误,因为这样的荒谬逻辑是他神学体系所需要的。柴与火同时都灭尽的看法,只是一种对养生说的曲从,并没有深究一下火与柴的根本关系。只有像他说的火可以传异薪,某一薪可以有尽时,而火都永远传下去,才是“远寻其类者也”,才能证明精神可以不依靠任何一个具体的形体而独立自存、永不消灭。
僧肇的佛教哲学思想体系
僧肇是东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理论家。僧肇的佛教哲学体系,从“本”、“末”,“有”、“无”,“名”、“实”,主体、客体等都没有独立的本性,即没有自性,论证世界原来是“空”的;从事物、现象之间绝无连续性,论证世界万物是永恒不变的;从必须去掉一切世俗的认识,即“惑智”,才能达到佛教所谓的“真智”,论证对“空”的认识只能用“无知”的“般若”(佛教所谓的智慧)。僧肇在这里涉及到了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哲学基本理论的各个方面。他的哲学形上学理论对以后佛教理论有很大影响。
“不真空论”。僧肇研究了当时流传的空宗各派对空宗根本理论“空”的各种不同说法。他说,有的只是简单地从主观方面排除万物对心的干扰,但并没有否认万物的存在。有的就事论事,只从物质现象不能自己形成,证明它不是物质的,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物质现象本来就不是真实的。
空宗关于“空”的理论,并没有简单地否认“有”和“无”的存在,而只是告诉人们这些“有”和“无”都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认为,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空”的意义,要从实质上来理解“空”的意义,即“有”和“无”都是不真实的存在,因此世界是“空”的。
他认为不能把“无”说得太绝对了,把“无”说得太绝对,容易与一般人的常识对立起来,因而不利于佛教理论的宣传和为人们所接受。他说,佛教真理(“真谛”)与世俗见解(“俗谛”)两种说法虽然不同,因为世俗的见解是从世界的现象方面看,因此认为万物是有,佛教真理是从世界的本质方面看,因此认为万物是非实有。
僧肇反对在“有”之外或“有”之上还有一个“无”的本体的说法,他认为应当是“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就是说,应该从万物本身去认识它的虚假,而不应该另立一个虚无,然后再说万物是虚假的。因此,在僧肇看来,承认现象的存在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的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客观物质现象,虽然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存在,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这种假象也是不存在的。就好像一种幻觉产生的人像,并不是没有幻化人这回事,而只是说幻化人不是真实的人罢了。因此,他认为正确地说,物既是“非有”又是“非无”。
僧肇一方面根据佛教“缘起”说(“缘”指各种条件)的理论证明物的“非有非无”。他说,现象既从“因缘”而生,因此它没有独立的本性(“自性”),不是独立、永恒的存在,不是真实的“有”;然而,它确实又由“缘”而起,因此,又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不存在,是绝对的虚空。我们说的不能把那种不存在认为是不存在,那是因为这种不存在不是绝对的虚空;我们说的不能把那种存在认为是存在,那是因为这种存在是不真实的存在。因此,如果认识到存在不是真实的,不存在不是毫无形迹,那么“有”和“无”虽然称谓不同,而他们达到的结论是一样的。
僧肇根据佛教的“缘起”说,根本否认事物有质的规定性,拿他的话来讲,就是没有“自性”,从而也就根本否定了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实在。因此,他虽然认为必须承认现象的存在,主张世界“非空”,然而他把现象都归结为各种条件的凑合,是虚假的幻象,非事物本质的反映,这样世界从根本上讲还是“非有”。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另一方面,僧肇又从哲学上常讲的“名”“实”关系来说明万物的“不真”。从物的名称去寻求物,物没有与这名称相当的实在。从物去探求名,名也没有反映物的功用。物没有与名称相当的实在,可见它不是名所指的物;名没有反映物的功用,可见它不是物的名。因此,名不和它的实相当,物也不和它的名相当。名与实既然互不相当,哪里还有什么所谓万物呢?“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所以说,万物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叫它作“物”,从来就只是一种假的称号。
我们认为,名词是表达概念的,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任何名词、概念,都是依赖于客观事物,并与一定的客观事物相符合(“当”)的。僧肇否认名必须依赖于客观实在的物,否认名是一定客观事物的反映,得出“假号”的结论,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客观世界万物的真实存在,从而为佛教“勘破红尘”的出世主义作理论论证。由此可见,僧肇所谓“然则非有非无者,信真谛之谈也”,把认为事物现象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观点当作佛教的最高真理,其实只是用一种更圆通的手法来宣扬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的大乘空宗理论。
他认为佛经就是通过佛教真理观阐明“非有”的道理,又通过世俗的见解阐明“非无”的道理,从而把这两者结合、一致起来。圣人之所以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历种种迷惑而永不迷惑,就是因为他“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认识到万物本来就是虚幻的,而不是凭借把万物说成是虚幻的,然后才认为是虚幻的。
“物不迁论”。一般常识的见解,认为万物都是生生灭灭变动不居的,可是佛教所要追求的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极乐世界”。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使佛教理论得以自圆其说,改变人们一般常识的见解,这就是僧肇著“物不迁论”的理论意义。
宣扬佛教真理,就会与世俗的见解不合;照顾了世俗的见解,又违反了佛教真理。违反佛教真理,会使人迷惑本性以至丧失本性;与世俗的见解不合,又会使佛教理论没有说服力。如何来调解这个矛盾呢?僧肇仍然运用调解“有”“无”的“不真空论”的办法。
佛教经典所谓的不变,并不是教人们离开了变化去寻求不变,而是要在变动中去认识不变。僧肇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比起汉初董仲舒直截了当地宣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理论,又要精致得多了。
首先,他认为一般人所谓事物的变化的根据是,过去的事物不会延续到现在,所以说事物是变动的,而不是不变的。其实这恰好说明事物是不变的,证明“物不相往来”。过去的东西,它本来就在过去的时间里,不应该从现在联系到过去;现在的东西,也本来就在现在的时间里,而不应该从过去联系到现在。这里,时间虽然有过去、现在、将来,但在各个时间阶段里的事物是没有延续、相联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事物是“不相往来”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称去而不迁”,即虽说消逝而并不变化。
僧肇的理论把时间的变化与物质运动对立起来,空谈时间上“过去”、“现在”、“将来”的变化,而根本否定事物在时间上变化的连续性,而把中断性绝对化。这样,他所讲的时间变化,只是一种空洞的框子,观念中存在的东西,而在实际上事物是根本没有任何运动、变化的。于是得出了物不相往来的结论。
其次,僧肇进一步提出了“物不相往来”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他所谓的“各性住于一世”的理论。他举例说,有一个出家人(梵志),少年时出家,头发白了才回到家乡,邻居们见了他就问,从前的梵志还在吗?梵志回答说,我好像当年的梵志,又不是当年的梵志。邻居们听了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他是乱说。为什么邻居们会感到惊讶和认为梵志是乱说呢?这是因为他们总认为人从少年到壮年是同一个躯体,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这个躯体。所以只知道年龄的消逝,而不知道人的躯体随着年龄一同变迁。
僧肇说,这也就好像人们总是在现在中去寻找过去,因为他们总认为事物是变化的。他则相反,要在过去中找现在,所以知道事物是不变的。为什么呢?如果说现在能联系到过去,过去就应该包括现在;过去能延续到现在,现在应该包括过去。但在实际上是“今而无古”,“古而无今”,现在既不包括过去,过去也不包括现在。因此,可以知道过去不会延续到现在,现在也不会延续到将来。
所以说事物各自都只是停留在一定阶段,没有发展、延续和变动。以梵志的例子来讲,按僧肇“各性住于一世”的理论来解释,就是少年的梵志只存在于梵志的少年时期,白发的梵志只是现在的梵志。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躯体的两个梵志。只能说白发的梵志好像少年的梵志,而不能说白发的梵志是由少年变来的。两个梵志好像有联系,所以也可以说有变动;但实际上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变动。僧肇这种理论的根本错误是否认事物质的变化的连续性。在他看来即使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它的质也是绝无连续的,甚至是根本不同的质。所有的连续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这就是僧肇“即动以求静”的本质:动是幻象,静是实质。
僧肇“物不迁论”的形而上学思想,也是为佛教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宗教迷信理论作论证的。根据“物不迁”的理论,所以佛经上说,尽管经历世界毁灭时期的三灾(水、火、风),而每人所造下的“业”(善、恶等活动)却永远抹不掉。这话是不错的。过去的因既已形成,不会消灭,也不会继续到现在而有所改变,那么现在受其果,得到报应,就是不能变更的。这样,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迷信理论就是不可动摇的法则了。一切宗教理论,最后都必然要归结到论证现实世界的“苦难”,宗教世界的“幸福”,结论是“出世”,即超脱现实世界。佛教就是用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来论证现实世界的“苦难”的。僧肇的形上学,尽管谈了许多玄虚的诡辩哲学,但在论证出世主义这一归结点上,他的理论目的也是十分鲜明的。
“般若无知论”。“般若”是佛教区别于一般人的智慧的所谓最高智慧。僧肇认为“般若”所以为最高之智慧,那在于它是“无知”。正由于它是无知,故能无所不知。
一般人所谓的智慧,都是以客观存在(“所知”)为对象的认识来说的,所以叫做有“知”。然而佛教所要认识的真理(“真谛”)不是一般所讲的对象,而是世界的本质“空。一般人所认识的对象是具体的客观存在,而佛教则认为这些具体的客观存在都不过是虚假的幻象,执著于对这些幻象的认识而得到的知识,那是一种产生种种烦恼的“惑智”。佛教要认识的是“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的世界本质“空”,这是不能用任何区分是非、彼此等世俗知识概念来表达的。所以佛教所谓的智慧根本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就它没有任何具体的认识来讲,也可以叫做“无知”,然而它却是解脱种种烦恼的“真智”。
对于这样一种不同于一般事物的、神秘主义虚构的世界本质——“空”,当然不能用一般的认识去认识它,不但一般的感性认识不能认识,而且一般的理性认识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它只能靠“般若”的“无知”去体会,也就是用不同于任何感性或理性的“知”的神秘主义直观去达到它。一般人所谓的知,只能认识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它有所知,就有其所不知。圣人的心(也就是佛教最高的智慧)不是认识一些具体的东西,而是认识“空”的世界本质,所以虽说无知,却是无所不知,乃至一切都知。
有所知,有所不知,这是认识的正常现象,人的认识正是由不知到知的辩证发展过程。僧肇从宗教神秘主义出发,否定一般人的正常认识规律,鼓吹“不知之知”,其目的也就是要根本否定认识的客观内容,否定真理的客观标准,而把宗教的说教当作惟一的真理,要人们相信解脱轮回的“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僧肇所讲的“般若无知”,也是一种带有十分神秘色彩的先验论。然而这种“无知”的“般若”却又是“无所不知”,“一切知”的“真知”。那么,这种“真知”是从哪里来的呢?僧肇说,这种“无知”的“真知”完全是自我产生的,本来具有的,根本不必依靠什么对象或条件才产生。
僧肇认为,这正是“圣人”的智慧区别于一般人认识的所在。所以,僧肇讲的“无知”“般若”完全是一种先验论。而且由于他认为“般若”是对佛教虚构的世界本质“空”的认识,因此这种先验论更带上了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同时,僧肇既认为把现象世界看成实有,都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世界本质是“空”造成的一种虚假幻象;而且认识世界本质的“空”,也只有通过神秘主义的直观、先验的“圣心”,这也就说明了他的整个宗教哲学体系的特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僧肇就是这样,通过“不真空”、“物不迁”的论证,肯定一个“空”的、永恒不变的精神世界的存在,然后又通过“般若无知”的论证,指出认识这个“空”的、不变的精神世界的可能和途径。这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在理论上完全是为出世主义的宗教世界观作论证的,而在现实社会上的作用则是:一方面为了麻醉人民群众,让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制度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为地主统治阶级上层的剥削生活辩护,并“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