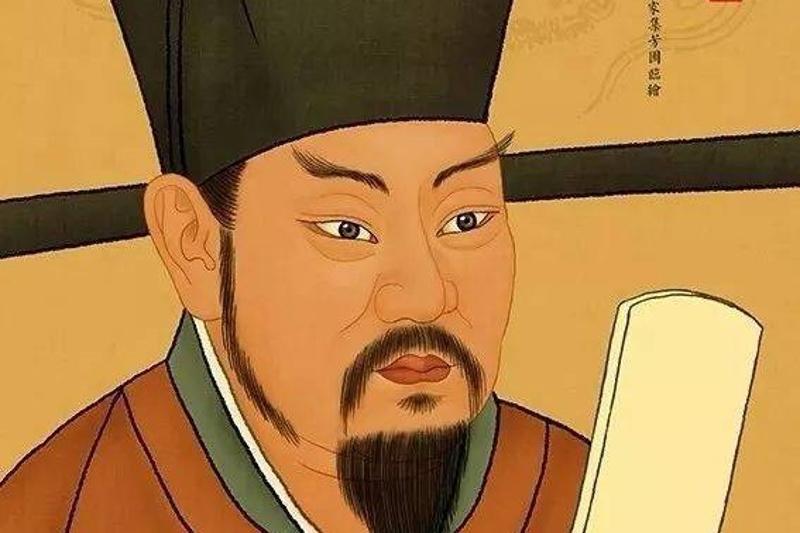东晋南北朝隋唐道教哲学的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概况
道教与佛教不同,它是我国自创的一种宗教。道教是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和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等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最早大约在东汉末,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而正式出现。其时在社会上有两大道教组织:一为于吉、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一为张陵(道教徒称为张道陵、张天师)所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为天师道)。它们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为经典,把老子道家思想改变成为道教的理论依据,因此,道家与道教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太平道、五斗米道为代表的早期道教,还只是一种民间宗教。它活动于下层民众中,并与农民起义相结合,起到了宣传和组织农民起义的作用。张角领导的太平道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推翻“苍天”(东汉皇朝),代之以“黄天”(农民起义军的政权)。其中有些五斗米道设置“义舍”,也与这种“救穷周急”的思想不无关系,而且是提倡下层劳动人民互助、互济的具体体现。地方还可窥见一些当时太平道反对剥削、压迫,要求均平的思想。
总的来讲,这时的道教还没有系统的教义和宗教理论。它的宗教活动的内容,还只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在民间流行的“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说”、“鬼神崇拜”等迷信活动的杂凑而已。此外,还规定了一些简单的宗教戒律。随着黄巾起义的被镇压,张鲁的被招降,初期道教作为民间宗教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此告终。
两晋以后,道教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使原有的民间道教变成为朝廷所支持的官方道教,从而使得道教无论在宗教教义和理论上,还是在宗教组织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道教走上了成熟发展的时期,形成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有唐一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大力支持,道教更为繁荣昌盛。宋元明时期,虽然道教宗派林立,组织更趋严密,道教典籍不断编纂刊印,对宋明理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它在教义和理论上已没有太多的新发展。明万历以后,道教趋于衰退。
道教的基本教义是追求长生不死而成神仙。在理论上,则主要是借用道家的学说,同时又吸收儒家和佛教的一些思想以为补充。道教把“道”作为其最高的最根本的信仰,把“道”看做是超时空的先天地万物的宗祖。认为“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包,是一切的开始。
为了适应宗教信仰的需要,道教还把“道”人格化为“三清尊神”,即所谓“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亦即“太上老君”、“老子”)。道教的道术(道教方术)十分杂多。这些道术中,有些是迷信,如求神、驱鬼、禳灾、祈福等;有些则是与体育、医药结合起来的养生之道。所以在道教典籍中,保留着一些我国古代有关化学、医学、体育锻炼等方面的有科学内容的资料。
葛洪和陶弘景的道教哲学思想
葛洪竭力把道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结合起来,以此他猛烈抨击张角等所开创的,反映下层人民要求的初期的民间道教为“邪道”、“鬼道”等。
在宗教信仰方面,葛洪虚构出了一个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至上神“元始天真”,并论证了神仙的存在。在道教哲学方面,则主要发挥了《老子》的关于“玄”、“道”、“一”、“无”等宇宙本原的思想,以论证得道成仙的学说。
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即所谓“玄者,自然之始祖。“玄”的作用是神通广大的,仅如此,玄还是无所不在的。“玄”超出于一切具体的“器”、“神”,而是一切“器”、“神”的主宰者。这样的“玄”不可能是物质的存在,只能是一种神秘的绝对物。正因为如此,葛洪对“玄”的所有描述只能是“玄之又玄”的了。即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正如葛洪自己所说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得之乎内”。然而他又认为:“其唯玄道,可与为永。”葛洪反复论证“玄道”超时空而永恒存在。
“玄”的概念,在《老子》那里与“道”的概念并不完全相等,《老子》是以“道”为先天地生的万物本原,而“玄”是描述“道”的神妙作用的。葛洪把“玄”也说成是“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这是吸收了西汉末年扬雄《太玄》中把“玄”作为宇宙本原的思想。所以,在葛洪那里,是把“玄”和“道”完全等同起来的。他对“道”的描述,基本上与“玄”一样。
葛洪还认为,“玄”或“道”虽能生出有形有象的万物,但它们本身,却是无形无象,不可名状,即所谓“其本无名”,或者径直就是“无”。“无”是最根本的,“有”只不过是“无”寄处的宫室而已。再则,“玄”和“道”虽然“鼓冶亿类”,“胞胎万类”,但其本身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即所谓“一”。所以,葛洪认为,要守住“玄”或“道”,也就是要守住“一”。“一”也就是“玄”和“道”。
葛洪从道教求仙通神的宗教教义出发,特别发挥了“守一存真,乃得通神”的思想。“真”也就是“一”,在葛洪看来,“一”是最真实的本体,所以“守一存真”,他也称为“守真一”。所以,他又认为“守一存真”是得“道”、存“玄”,通向神仙之境的根本功夫。“一”,葛洪既称之为“真一”,又称之为“玄一”。“玄一”的功能与“真一”相同,但又认为“玄一”似乎比“真一”容易达到,两者似有些区别。
葛洪还认为,“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即修道之难在于坚守“真一”而不失。为什么“守真一”如此之难呢?他说世俗之人所以不能守住“纯一”(亦即“真一”),那是由于物欲嗜好过多,而又没有杜绝、遏制的“检括”(即指矫正邪曲的工具)。那么,如何才能守住“真一”呢?只有通过宗教禁欲主义的修养,才能达到“守真一”,求得神仙境界。由此可见,葛洪所谓的“玄”、“道”、“无”、“一”,完全是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本体。
在形神关系上,当时的道教比较注重炼形,就这一点讲,葛洪有时把形、神关系比喻为“堤”和“水”,“烛”和“火”的关系。由于道教注重炼形的目的是为了使神不离其身,从而达到长生不死而成仙,所以葛洪虽然认为形神是互相依靠的,而又把形说成要依赖于神才能不朽不疲,从而又强调了神比形更为重要。
葛洪是历史上著名的炼丹学家,提倡服食丹药寻求长生成为神仙。所以他特别注意炼丹术的研究和医药学的研究。不过他的炼丹这完全是一种宗教神学的说法了。但是他对医药学和炼丹术的研究,对我国古代医药学和化学的发展,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陶弘景在道教史上影响很大,他是茅山宗的开创者。他在《真灵位业图》一书中,按照儒家所倡导的世俗社会的等级秩序,建构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该书把道教所信仰的天神、地祇、人鬼和仙真共分了七个等级。同时,他又以神仙世界的等级品第,反过来论证世俗社会分别贵贱、高低的合理性。除此之外,他还构建了一套道生元气生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思想。
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人的道教哲学思想
隋统一南北后,曾大力提倡佛教,同时对道教也不排斥。隋朝政权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即为李唐王朝所取代。唐王朝适应统一形势的需要,基本上是采取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政策,同时用来加强思想统治。儒家居主导地位,辅之以佛、道二教。唐王朝帝室姓李,曾以此攀太上老君李耳为始祖,提高道教的地位。当然,反过来也为了借神权以提高皇室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割据对峙,不相通问,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南北各立不同流派。至唐朝,与政治、经济的统一相适应,佛教、道教的南北流派也有融合、统一的趋势。
成玄英以道教宗教观点注释《老子》和《庄子》,他的重点在阐发所谓“重玄之道”。“重玄之道”本于《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一语。在一部分道教徒看来,《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即“重玄之道”,是求道成仙的要诀,是《老子》论“道”的精义所在。
所谓“重玄之道”,这是说对于客观世界不论是坚持说它“有”,还是说它“无”,都是有所执著的表现,都是不对的。正确的认识应当是,既不执著于“有”,又不执著于“无”。不仅如此,进而对于不执著于“有”或“无”这种看法,也不应当执著不放,这就是所谓“重玄之道”,亦即“玄之又玄”的精义。所以,他所讲的道教的“重玄之道”,是一种“非有非无”的本体。成玄英这里引佛入道,用的是佛教论证客观世界虚幻不实的“双遣法”,以说明“道”与“万物”,“有”和“无”之间的关系。
成玄英对于“道”有一详细的论述,“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万物均由“道”生成。“道”的特点是:“虚无”等。但“道”生成万物,万物都以“道”为本,则又是“有”。所谓“无端”、“无对”、“不移”,都是说明“道”是完整而不可分,独立而永存的。而以“道”为本体的万物,又是“有极”、“必亏”的。总之,“道”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绝对本体。“道”虽然是至虚至无,但它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绝对本体;天地万物虽然是有形有象,但它是虚幻不实的“空”、“无”。
成玄英既不同意把天地万物看成是实有,也反对把客观世界看成是绝对的空无。他是主张“即本(道)即迹(万物),即体即用,空有双照,动寂一时”。只要觉悟到客观世界是虚假的,主观感觉也是不真实的,那么即使在生活上穷极耳目享受,也可以求得仙道的境界,不必闭目塞听,断情忍色。
成玄英的这些思想,是对郭象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发挥。只不过他从宗教神学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补充,为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求道成仙也不必脱离世俗的生活享受和政治活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而已。
王玄览也是以佛教思想来充实道教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道教神学理论,讨论了道与众生的关系。他认为,“万物禀道生”,道与万物不是“有”“无”的区别,而是“隐”“显”的不同。道与万物之间他认为有同亦有异。
“道”,并不在人心之外,而就是人心中具有的“道性”。修道不应外求,而应当内求。所以,他所讲的“道”生万物,也就是“心”生万物。总之,他认为,“心之与境,常以心为主”。也就是说,客观事物依赖于主观感觉。这种根本否定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并把它归结为主观意识的产物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
所以,王玄览认为,道教修道成仙的要旨,是要修得一个清净不变的“识体”。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大乘有宗唯识宗的影响,而附会以道教教义提出来的道教神学理论。
司马承祯在道教中,不注重炼丹、服食、变化等道术,而提倡静修正心。他大量吸收佛教宗教理论和传统的儒家关于正心诚意的修养方法,把它们和道教的宗教思想结合起来。他的一些关于“主静”的理论,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
司马承祯认为,“道”是一种神妙莫测的东西。人如果能得到它,就可以长生不死。他认为,人要得到“道”,关键在于“修心”。而“修心”的关键又在于“主静去欲”。只有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才能得到道而生智慧,心动则是产生昏乱的根源。要达到心静,则必须首先觉悟客观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从而去掉种种欲求,达到“虚心”、“安心”。
关于“主静”的修养方法,司马承祯说要从客观现实生活中把自己摆脱出来,“不著一物”。不仅如此,还需要对外物一点意念都不许发生,“收心离境”。而要做到“收心离境”,对外物不起一点意念,就要把对外物的认识,移向对自我的认识。司马承祯称此为“存想”。这些修养方法,很显然是从佛教所谓禅定、止观的方法脱化而来的。所以,有时他把这种方法径直称之为“定”。这是他引导人们脱离现实世界,进入他道教精神境界的第一步功夫。
他认为,进一步的修炼功夫是要达到“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的境界。人们如果一旦达到这种“泰定”的境界,就能“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由此可见,司马承祯的“主静”说,是想通过物我双遣,而引导人们进入一种完全寂静空虚的精神境界。
司马承祯还认为,他所讲的“主静”,也并不是“执心住空”。因为“静”,并不是简单地把外物看做空无,也不是不分是非简单地把一切意念断绝。他认为,在修炼上要防止四种偏向,第一种偏向是“永断知觉”,第二种偏向是“一无所制”,这在司马承祯看来是走了两个极端。第三种偏向是“心无指归”,“待自空者”,这是不懂得修炼要“以道为本”,放弃了主观的努力。第四种偏向是言行不一。那么怎样才是达到真正的“静”或“定”呢?他说只要做到主观上不追求外物,又不为外物的引诱而动心,这就是“真定正基”,也即达到了心的真正的“安”或“静”了。司马承祯的这种“主静”方法,与宋代理学所讲的“无欲故静”的“主静”功夫(周敦颐)、“惩忿窒欲”的“居敬”功夫(朱熹)等有相似之处,因而为宋明理学所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