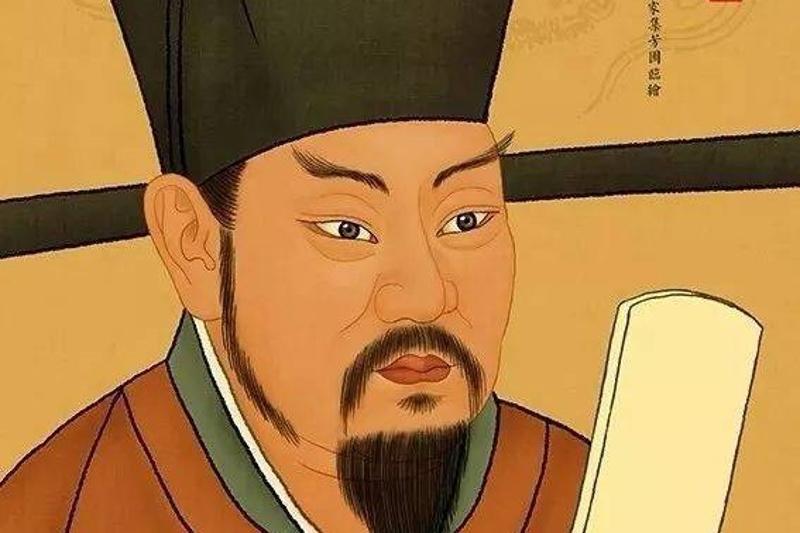裴頠和欧阳建
裴頠[危页]等反对玄学贵无论的历史背景
西晋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时却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但门阀士族是一个十分腐朽的阶层,在表面上他们又都装出一付对物质欲望十分淡薄和清高的样子,高唱“无为”、“无欲”的调子。魏正始年间发展起来的玄学贵无论到西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其流弊以至于不务政事、不遵礼教的社会风气盛行。
他集中批判了“无为”的说教,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无为”,“无为”对治理群生,维护名教,没有任何益处。调养既已存在的万有,不是“无用”所能达到的;治理既已存在着的众多事物,也不是“无为”所能驯服的。因此,必须“有为”。
他从维护封建名教,反对政治上的“无为”出发批判玄学“贵无”论,进而对其唯心主义理论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理论。
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杨泉,他坚持了以物质原因来说明天地万物的生存和变化,这是与玄学唯心主义以“无”为天地万物之本的观点根本对立的。
裴頠的“崇有论”思想
裴頠的“崇有”论是针对王弼等玄学“贵无”论提出来的。他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王弼一派“以无为本”的思想。
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而“有”只是“无”的表现。裴頠[危页]首先反对在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什么本体。他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它成为“有”,而是它“自生”、“自有”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有”是说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事物都是有形有象的,所以,有形有象也就是事物的本体。“无”只不过是“有”的一种消失了的状况。这个观点排斥了“无”的绝对性、永恒性、至上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弼等“以无为本”的观点。
在王弼看来,个体事物总有其局限性,不能自存,万有必须以“无”为其本体,才能存在。所以,“无”是“有”的全体的本体,整个万有都以“无”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裴頠驳斥说,整个万有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道”,就是万有自身,“道”无非是指万有的总和,离开万有也就没有“道”。这也就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上否定了王弼“以无为本”的观点。
王弼还把事物的规律和事物本身割裂开来,从而把规律(“理”)看成是本体“无”的产物。裴頠[危页]认为规律是表现在事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之中。“理”是以“有”作为它存在的根据的。这就驳斥了王弼到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变化根源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王弼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能温则不能凉,而且温自身也不能为,必须有一个不温不凉的东西作为万有的本体,万有才能共存。裴頠[危页]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全体的一部分,都有其规定性,因此不能“自足”,而需要依靠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条件。
事物的存在要依靠条件,条件适合于某一事物的存在,对于某一事物来说就叫做“宜”,事物选择其适合存在的条件,就叫合乎实际,也就是说,每个事物的存在,总是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裴頠在反对贵无论的斗争中,阐明了世界上一存在着的就是“有”,即个体事物,具体的“有”都是有条件的,是互相依靠的,但却不需要一个“无”的本体支持它们。这是裴[插图]的《崇有论》对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裴頠[危页]说的“有”,不仅指自然物,也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事物,如封建礼教之类的事物。因此,他从崇有论出发,又肯定了贵贱等级的合理性,他说:“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这又为封建等级制度作了辩护。这样,他以后的哲学家又从这里引出凡现存的“有”都是合理的观点,郭象正是这样从右的方面发展了裴頠的思想。
然而他的《崇有论》只看到个体事物的实在性,在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回避了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问题,从而认为事物都是“始生者,自生”,这又否认了个体事物之间的转化,陷入了形而上学。这种观点,后来又被郭象发展为“独化”说。
欧阳建“言尽意论”的认识论
“意”
大体上是指思想内容的意思。
“言”
是指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工具。
当时,有所谓“言意之辩”,表面上是讨论语言是否能反映思想内容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客观世界能不能认识或事物的本体能不能认识的问题。
荀粲等玄学家提倡“言不尽意”,认为义理存于现象之外,“象外之意”是不能由人们的感官或思维来认识的,因此语言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不可知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反对了这种不可知论,同时也打击了王弼的“得意忘象”的理论。
例如王弼认为本来圣人立言为了教化众人修身养性,可是后来圣人的教化的原意在烦琐的章句中被湮没了;必须忘言忘象,这样才可能以天道为法则而行于大化。王弼的这种观点是企图从反对汉儒的烦琐章句之学中来建立他的哲学体系。
欧阳建针对上述“言不尽意”的观点分析说:形之方圆、色之黑白,不依赖于“名”、“称”就自然明白,就可以直接感受或意会得到。“名”与“言”对于了解和认识“物”与“理”不起什么作用,没有必然联系,不一定相一致。正因为如此,“言不尽意”论者对“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无法理解。
由于“物”与“理”的变化和不同,“名”与“称”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和不同。正因为如此,“名”、“称”对于“物”、“理”不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对“名”、“称”的正确规定,通过语言的分析和辩论,对于交流思想和正确地认识“物”、“理”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不用语言(概念)就不能表达出来。因为事物客观地存在于外界,不用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就不能加以区别。如果不用语言表达人们的认识,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无法交流;用概念把认识明晰的表达出来,就可以分辨事物不同的品类;语言概念和它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相一致,人们之间才可以有思想和感情的交流。
欧阳建直接讲的是语言的社会功用的问题。因为语言是手段和工具,人们可以利用它来彼此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同时,他这里也是讲的认识论问题,认为概念能够反映事物,以及事物必须用概念来反映,因为他说的是:“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欧阳建肯定了人们可以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否定了唯心主义的“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
欧阳建认为语言和概念来源于客观事物,反映着客观事物,概念是由人们约定而成的反映事物本身的符号。语言要根据事物道理的变化而变化的。此事物为什么叫此名,而不叫别的名称,那是人们约定的。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所以归根到底“名”是根据事物的不同而不同的
从认识论上说,欧阳建接触到两个问题,一是语言概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语言概念是根据客观事物而有,因此它是有根据的;二是语言概念只是根据客观事物而有的,它不是事物本身。这里,欧阳建既看到了语言概念和客观事物的区别,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欧阳建在批判“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中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